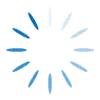赵铮蹲在她身边,就着微光,看着本子上那些歪歪扭扭却无比认真的字迹和符号。
有些是字,有些是只有她自己才懂的标记,画着稻穗、虫子、水滴和太阳。他看不懂全部,却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份滚烫的热忱。
赵铮轻轻握住她沾着泥星子的手腕,粗糙的指腹在她磨红的手背上轻轻摩挲着,低沉的嗓音里满是动容:“玲珑,你真了不起。”
灶膛里的火苗跳跃着,映亮了阮玲珑写满专注的侧脸。
她伏在院中那张小石桌上,就着油灯昏黄的光,仔细地将白天记录在炭笔小本上的零散信息,工整地誊写到另一个稍大些的本子上。
“今日,甲字一号对照田,播本地稻种,行距六寸,株距三寸,底肥为腐熟猪粪五担。”*
“乙字二号、三号田,播‘玲珑金穗一号’,这是她给自己培育的稻种取的名字,行距一尺,株距四寸。底肥:厨余草木灰混合肥三担,腐熟程度待李伯二次确认;另加河底淤泥两担,这是张伯的建议,可增地力保墒情。”
“丙字四号田,半亩‘玲珑金穗一号’,行株距同乙字田,底肥仅用腐熟猪粪三担,以作对比。”
“丁字五号田,半亩本地稻谷种,行株距同甲字田,底肥试用‘玲珑牌混合肥料’三担。”
她写得极其认真,不仅记录了具体的操作,还写下了三位老农的每一条意见和自己的思考。
“陈伯言:株距过宽恐减产。记:待抽穗期观察分蘖数及穗粒饱满度对比甲字田。”
“李伯言:混合肥劲足,需深埋防烧根。已照做。记:待出苗后观察苗情。”
“张伯言:河湾地湿,需防稻飞虱和二化螟,可于田埂四周撒草木灰或茶籽饼粉。明日备料。另,水资源珍贵,浇灌必于寅时(凌晨三点到五点)或酉时(下午五点到七点),避日头。切记!”
油灯的灯芯爆出一个灯花,发出轻微的噼啪声。阮玲珑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睛,低头沉思。
关于如何使用木系异能,初期她打算仅以微量异能温和滋养‘玲珑金穗一号’种子,促其根系深扎,增强抗旱力,绝不催熟。重点观察其在自然条件下,配合改良土壤的实际表现。每日记录苗高、叶色、墒情(土壤湿度)。
想到抗旱力,阮玲珑的指尖无意识地轻敲桌面。
窗外,夜色沉沉,依旧没有一丝下雨的征兆。
最后,阮玲珑起身合上本子,吹熄了油灯。小院陷入一片寂静的黑暗,只有篱笆下新栽的蔷薇藤蔓,在无人察觉的夜色里,感应着主人深沉的心念,极其缓慢地舒展出更坚韧的嫩芽,悄然指向星辰的方向。
47
第47章 惊雷
◎黄天泽以为来人是神医徐闻道,没想到他竟然在平安镇看到了因病去世的庆王妃文静!◎
平安镇的夏日,被一种无形的焦灼炙烤着。
风是滚烫的,卷起街面上的浮尘,扑在行人汗津津的脸上,带来一阵粗粝的刺痛,让人不由得心生浮躁。
空气干燥得仿佛一点火星就能燎原,吸进肺里都带着火烧火燎的涩意。街头巷尾,往日的喧闹像是被这毒日头蒸干了水分,只余下一种沉闷的压抑。
赵铮的肉摊前,熟客胡婶挎着空了大半的菜篮,对着案板上仅剩的几块边角肉叹了口气,布满愁纹的脸皱得更紧。
“赵家小子,今儿少割二两肉吧。家里那点麦子,磨出来全是麸皮,连稀疙瘩汤都快喝不上了,哪还有闲钱买肉啊。”
她粗糙的手指捻着几个磨得发亮的铜板,犹豫再三,还是只买了一块最便宜的猪油膘,准备回去熬点油星拌野菜。
赵铮沉默地点点头,他利落地切下那块肥膘,用荷叶包好递过去,顺手又添了一小根剔得干干净净的筒子骨。
“婶子,这骨头拿回去熬点汤水,好歹沾点荤腥。”
王婶眼圈一红,嘴唇哆嗦着,最终只是低低道了声谢,她佝偻着背脊,脚步沉重地离开了。
这样的场景,近几日每天都在东市口上演。赵铮案板上零售的猪肉,已经从每日两头猪的分量,减少到了一头,甚至有时连一头猪的肉都卖不完。
赵铮只好把卖剩的猪肉全都制作成熏肉,毕竟天气热,鲜肉存放不得。
买肉的人少了,买得也越发抠搜。一张张日渐熟悉的街坊面孔,无一不带着被生计重压碾过的疲惫和愁苦,他们眼神黯淡,连说话的声音都低哑了几分。
原因无他,夏收结束了。
平安镇周遭十里八乡的麦田,在持续数月的高温的炙烤下,结出的麦穗稀稀拉拉,干瘪得像营养不良的孩子。
大山脚下的村子里,老王叔蹲在自家小院门口,抓起一把今年收获的麦粒,麦粒又小又轻,其中夹杂着大量的空壳。
老王叔粗糙的手掌掂量着手里的麦粒,浑浊的老泪无声地淌进干裂的泥土里。
一亩地,麦粒连皮带壳,才收不足一石半。除去提前缴纳的秋粮,剩下的那点麦子,磨出的面粉只够全家勒紧裤腰带喝两个月稀疙瘩汤。
偏偏这时候的粮价,像是火堆上的火苗,一天一个样地往上蹿。
平安镇的粮铺门口排起了长龙,恐慌和绝望如同瘟疫般在人群中无声蔓延。
这不仅仅是饥饿的威胁,更是对未来的无望。晚稻刚种下去不久,玉米、地瓜、高粱同样长势不好,老天爷依旧没有一丝下雨的意思。
河沟的水位一日低过一日,井水也开始变得浑浊吝啬。
赵铮今天收摊比往日早了许多。他推着空了一半的推车回到小院,空气中弥漫的沉闷并未因院墙的阻隔而消散。
他刚刚走进院门,便看到正蹲在菜畦边,小心翼翼给几株蔫头耷脑的菜苗浇水的阮玲珑。她的背影依旧单薄,但脊背挺得笔直,带着一种与周遭颓丧格格不入的韧劲。
“玲珑,镇上最近……”赵铮将车停好,声音低沉地开了个头。
阮玲珑回头看了赵铮一眼,然后专注地将最后一点宝贵的井水浇在菜根上,“铮哥,我知道你想说什么,老王叔家只收了一石半麦子。河对岸的李家村,听说更惨,一亩地才收一石。今年麦子产量比往年少了一半还多。”
她的声音平静,却像沉重的石头砸在赵铮心上。
“我们山里还有……”赵铮想说些什么。
阮玲珑终于站起身,她拍了拍手上的泥土,看向赵铮时脸上没有多少惊惶,只有对未来天气的不乐观。
“那八十石粮食,是我们的退路,不到万不得已,不能动,更不能露白。”
阮玲珑走到赵铮身边,握住了他沾着油腻和血腥气的大手,指尖冰凉却有力,“铮哥,我不怕饿肚子。但我怕……怕这旱情再继续下去,到时候,更可怕的事情会相继发生。”
来自末世的经历,那种饿殍遍野、秩序崩坏的恐怖景象,是她最深沉的梦魇。
赵铮反手紧紧握住她的手,粗糙的掌心传递着无声的承诺和力量,“玲珑,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”
他们的小院,仿佛成了这片绝望旱海中唯一一艘尚算安稳的小舟,但舟外惊涛骇浪,随时可能将一切吞噬。
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闷几乎要将整个平安镇压垮时,一个从天而降的好消息,伴随着飞扬的尘土和驿马急促的蹄声,轰然炸响在平安镇的上空。
“大捷,北境大捷!庆王爷神威!把北狄蛮子打趴下啦!”
报信的驿卒骑着快马,旋风般冲过平安镇的青石板路,他那嘶哑却亢奋的报喜声穿透了沉闷的空气。
“庆王爷阵前连斩北狄七员大将,逼得那北狄可汗跪地献上降书!”
“北狄认输了,赔款割地!咱大周赢了!”
“庆王爷威武!战神再世啊!”
打了胜仗的消息就像燎原的野火,瞬间点燃了原本死气沉沉的平安镇。
街头巷尾,蔫头耷脑的人们猛地抬起了头,黯淡的眼中迸发出难以置信的亮光,大家随即被这巨大的狂喜淹没。
“赢了,真的赢了?不打仗了?”
“庆王爷,是庆王爷!我就知道!有庆王爷在,北狄蛮子算个屁!”
“老天开眼啊,不打仗就好,不打仗就好啊!”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激动得老泪纵横,他经历过太多兵祸造成的惨烈场景,深知和平的珍贵。
“庆王爷千岁!千千岁!”
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嗓子,很快,压抑了许久的欢呼声如同决堤的洪水,在平安镇的大街小巷爆发出来。
沉闷的空气被一扫而空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劫后余生般的狂喜和振奋。
粮价依旧高企,旱情依然严峻,但“边境战争结束”这个消息,像一剂强效的定心丸,暂时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最大恐惧:兵灾。
只要不打仗,只要这世道还能安稳,总还有活下去的希望。
赵铮肉摊的生意似乎也短暂地回温了一些,不少人终于舍得割上二两肉,说要“沾沾庆王爷的喜气”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