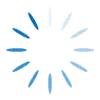“宝宝,别这样对我……”他的声音都在发颤,“我错了,我真的错了。你想要什么?我都可以给你。我把城南那套别墅转到你名下好不好?你不是喜欢珠宝吗?我都可以给你……”
秦玉桐静静地听着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她甚至没有试图抽回自己的手,就那么任由他握着,像握着一块没有温度的玉石。
见她不为所动,陆朝眼中的恐慌更甚。猛地收紧手指,将她的手按在自己心口的位置,隔着丝滑的布料,那颗心在疯狂地、杂乱无章地跳动。
“你摸摸看,”他几乎是在哀求,“它为你跳的。秦玉桐,你不能这么狠心……我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才让你属于我,你怎么可以说结束就结束?
“当初你救过我,我记得。”秦玉桐目光缓缓移到他的脸上,“你说,我这条命是你给的,所以我要听你的。”
她抓起他的手,按在自己纤细的脖颈上。
少女的皮肤细腻而冰冷,脆弱的颈动脉就在他的掌心下,一下,一下,微弱地跳动着。只要他稍稍用力,这抹鲜活的生命就会在他手中终结。
她说要把命还给他。
他怎么舍得?
这个念头疯了一样地蹿进脑海。
他费尽心机,不择手段,把她从江临身边抢过来,在她身上刻下自己的烙印,不是为了要她的命。
他是想要她这个人,活生生的,会哭会笑,会脸红心跳的秦玉桐。
陆朝猛地甩开她的手,像是被烫到一样,踉跄着后退了两步。他眼眶猩红,胸口剧烈地起伏。
客厅里陷入了漫长的沉默,只有雨声依旧。
不知过了多久,陆朝终于抬起头,那双深邃的眼眸里,霸道和强势褪去,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偏执和……哀求。
“最后一次。”他沙哑着嗓子开口,“再陪我最后一次。就当是……两不相欠。”
他妥协了。
用这种近乎卑微的方式。
秦玉桐看着他,没有说话。
“最后一次,”他重复道,声音里带着孤注一掷的意味,“之后,我放你走,我保证,再也不会去打扰你和……江临。”
窗外,一道闪电划破夜空,将他苍白的脸照得一清二楚。
秦玉桐忽然觉得有些可笑。
原来不可一世的陆朝,也会有这样的一天。
“好。”
她听到自己说。
他眼里的光,瞬间亮了起来。那是一种失而复得的狂喜,混杂着即将失去的痛苦,矛盾而炙热。
他没有再说话,只是走过来,一把将她横抱起来。
这一次,他的动作很轻,没有了之前的粗暴和不容抗拒,反而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小心翼翼。
她没有挣扎,任由他抱着自己走上旋梯,走进那间卧室。
他把她放在柔软的大床上,没有急着脱她的衣服,而是俯下身,先用指腹轻轻擦去她脸颊上的雨水。他的指尖滚烫,触碰到她冰冷的皮肤,两人同时瑟缩了一下。
他开始吻她。
从额头,到眉心,眼皮,再到鼻尖,最后才落在她的唇上。
这个吻,没有了之前的掠夺和侵占,只剩下缱绻的描摹和反复的碾转。
湿透的校服被一件件剥落,冰冷的空气让她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他用自己的身体笼罩住她,用体温将她一点点捂热。
窗外的雨越下越大,房间里却温暖如春。
他埋首在她颈间,嗅着她身上那股淡淡的幽香,一遍又一遍地,用一种近乎呢喃的语气,叫着她的名字。
“秦玉桐……”
“秦玉桐……”
她闭眼睛,任由他在自己身上点燃一簇又一簇的火。他的手抚过她的每一寸肌肤,带着一种末日来临般的绝望和痴迷。
动作间带着孤注一掷的凶狠,又有一种近乎崩坏的温柔。汗水从他紧实的背脊滑落,滴在秦玉桐的锁骨上。
窗外暴雨如注,雷声滚滚,像一头发怒的巨兽在天地间咆哮。
卧室里却安静得只剩下两人纠缠的呼吸,床架不堪重负的吱呀声,以及皮肤相贴时粘稠湿热的声响。
这是一场盛大而绝望的祭祀。
陆朝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祭出去,试图在她身上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。
他一遍遍地吻她,从紧闭的眼到颤抖的唇,力道大得像是要将她吞吃入腹。他进入得那么深,每一次撞击都仿佛要将自己的灵魂楔进她的身体里。
“秦玉桐……”他含糊地叫着她的名字,“看着我……求你,看着我。”
秦玉桐缓缓睁开眼。
水晶吊灯的光线刺得她眼眶发酸,视线里,是陆朝那张因情欲和痛苦而扭曲的脸。
他的眼眶是红的,浓密的睫毛上甚至挂着湿意,那双一向睥睨众生的黑眸里,此刻只剩下赤裸裸的乞求。
她没有回应,也没有躲闪。像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,在审视一出与自己无关的独角戏。
她的身体是诚实的,在这场极致的感官盛宴中战栗、蜷缩、攀上顶峰。可她的眼神,自始至终,清醒得像一块冰。
这块冰,彻底冻伤了陆朝。
他所有的疯狂和痴迷,在她清冷的注视下,都变成了一个笑话。
最后,他将脸深深埋进她的颈窝。温热的液体,一滴一滴,落在她的皮肤上。
是汗,还是泪,已经分不清了。
这场最后的告别,做得太过忘情,以至于谁都没有注意到,那扇厚重的卧室门,在他抱她进来时,只被随手带上,门锁的卡榫并未完全扣合,在风的对流下,虚掩着一道缝隙。
*
同一时间,一辆黑色的川崎,停在了陆家别墅的门外。
江临熄了火,长腿撑地。他摘下头盔,露出一张在夜色里也难掩清俊的脸。眼尾狭长,左眼下的那颗泪痣给他平添了几分冷感。雨水顺着他利落的短发滑下,他毫不在意地用手抹了一把脸。
母亲和那个男人出国旅游了,让他来拿忘掉的戒指寄给她。
偏偏忘了,偏偏是今天,偏偏……是他。
江临有些不耐地啧了一声。她总是喜欢使唤自己。但还是用密码打开了大门。
玄关一片漆黑,只有他带进来的风雨声。他随手按下开关,水晶吊灯骤然亮起,照得一室辉煌,也照得一室冷清。
“陆朝?”他喊了一声,换了鞋往里走。
没人应。
空气里有股若有似无的香气。
他没多想,径直走向二楼。
实木楼梯踩上去,发出沉闷的声响。越往上走,那股味道似乎越浓,还混杂着一些别的、更具侵略性的气息。
更奇怪的是,他好像听到了一点别的声音。
很轻,断断续续,被淹没在哗啦啦的雨声里。
像是什么东西的撞击声,又像是……女人压抑的不成调的呜咽。
江临的脚步停在了二楼走廊的尽头。
声音是从陆朝的卧室传来的。
他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他告诉自己别多想,也许是陆朝在看电影,那家伙品味恶俗,就喜欢看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他抬步,朝那扇虚掩的门走去。
越近,那声音越清晰。
女人的喘息,男人的低吼,交织成一张靡乱的网,兜头将他罩住。
那女人的声音……
他太熟悉了。那是他每晚都会在梦里听见的声音,是耍赖撒娇时,会无奈地叹气的声音,是他玩CS时,坐在他旁边,小声为他加油的声音。
是秦玉桐。
他僵在原地,连呼吸都忘了。
那道门缝,像地狱的入口,散发着引诱人窥探的、罪恶的吸力。
缝隙很窄,江临只能看到一片混乱的景象。
深色的丝质床单上,交迭着两具白得晃眼的身体。女孩黑色的长发像海藻一样铺散在枕头上,一张小脸泛着不正常的潮红,嘴唇被吻得红肿,正仰着纤细的脖颈,发出娇媚的呻吟。
而压在她身上的男人,他只看到一个宽阔结实的背。
但那已经足够了。
“轰——”
窗外一道闪电劈过,惨白的光一瞬间照亮了室内。
江临看清了,是陆朝。
而秦玉桐,他的女孩,正曲着腿,缠在陆朝的腰上。
江临猛地别开脸,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他扶着墙,才勉强站稳。
背叛。
这两个字狠狠扎进他的心脏,再搅烂他的五脏六腑。
他想起这几天秦玉桐的反常。她总是走神,眼下有淡淡的青黑,他问她怎么了,她只说是没睡好。
他信了。
他以为她是学习压力大。
他甚至还傻乎乎地安慰她,说等他考完大学,就带她去旅游散心。
原来,她不是没睡好。
她是在别人的床上,没睡好。
江临低头,看着自己手臂上那个鸢尾花的纹身。秦玉桐的名字里有个“桐”,他却觉得她更像鸢尾。高贵,神秘,又带着一丝忧郁。是他触不可及,只能小心翼翼捧在手心的神明。
可现在,他的神明,正在别的男人的身下辗转承欢。
像一个天大的笑话,一个耻辱的烙印,烫得他皮肤阵阵刺痛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