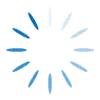香山北麓,玉泉山静卧于京西的晨霭之中。这里毗邻颐和园,自古便是皇家禁苑,风水极佳。时至今日,依旧是许多高级干部和退居二线的老领导择居之所。高墙电网隐于浓密的绿荫之后,哨岗看似稀疏,实则视野交错,毫无死角。每一条蜿蜒而入的柏油小路,都可能通向某处深不可测的宅邸。冬日的清晨,连鸟鸣都显得格外克制。
唐家大宅,陈汉升直挺挺的跪在青石板地上,和院子里堆砌成景的太湖石为伴,几竿翠竹在晨风中摇曳,发出沙沙轻响。
初冬的气温已经零下,他只穿着一件单薄的黑色衬衫,西装外套随意扔在一旁的地上。虽然跪着,但是腰背甚至比平时更加挺直,明明是负荆请罪,倒叫他跪出一种隐忍又挑衅的嚣张感。皮肤表面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,但肌肉却因紧绷和某种亢奋而微微发热。
二楼东侧的主卧室,厚重的窗帘被掀开。
唐怡几乎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窗棂上,大半个身体探出窗外,凌乱的发丝被寒风吹得拂过她毫无血色的脸颊。她刚刚能勉强下床,每一下呼吸都牵扯着腹腔深处的伤口,带来阵阵隐痛。曾经明艳张扬的脸庞如今血色尽失,眼窝深陷,干裂起皮的嘴唇不受控制地微微哆嗦。
唯有那双死死盯着楼下院子的眼睛,仿佛要将楼下那个身影生吞活剥。
“杀了他……我要杀了他!!”她的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,像是破旧的风箱在艰难抽动,身体控制不住地剧烈颤抖。看到陈汉升竟然出现在她家院子里,她所有的理智瞬间崩塌,恨不得立刻从窗口跳下去,用指甲撕烂他的脸,用牙齿咬断他的喉咙!
他怎么还敢来这里!指定网址不迷路:miren8.com
身后的两名保姆吓得魂飞魄散,慌忙从后面死死抱住她。如今的唐怡轻得像一片羽毛,流产加上后续感染和大出血的折腾,早已元气大伤,虚弱无力,轻易就被两个保姆半强制地搀离窗边,她们几乎是架着她,重新按回柔软的床上躺着。
唐母苏文金红着眼圈,急步上前,显然也是一夜未眠。她连忙指挥人将窗户关上,彻底隔绝了楼下的场景,拉上窗帘, 室内重新被温暖的空气填满。她坐在床沿,握住女儿冰凉而颤抖的手,未语泪先流,声音哽咽着劝慰:“囡囡,我苦命的囡囡。你得听话,现在是一点风都不能沾,月子里若是落下病根,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啊……你得好好养着,什么都别想……”
“月子?”唐怡像是被这两个字狠狠刺了一下,干涸的眼眶里竟又硬生生逼出几滴泪,“我还有什么月子?我还有什么一辈子!”她反手抓住母亲的手腕,指甲用力得几乎要掐进对方的皮肉里,眼神癫狂而绝望,“妈!是他害了我,是他把我变成这个鬼样子的!不能放过他,绝对不能!我要他死!我要亲眼看着他不得好死!”
那些被药物模糊了的恐怖记忆再次汹涌袭来。昏暗迷离的灯光,扭曲如鬼魅的人影,混杂着烟酒和劣质香水的陌生男人气息,撕心裂肺的剧痛,还有最后被无边无际的血色彻底淹没……等她从死亡的边缘被抢救回来,得到的是一纸冰冷无情的诊断。
她永远地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,也几乎被剥夺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完整。昔日骄傲的唐家大小姐,如今只剩下一具破败的空壳和满腔的仇恨。
如今,唯有滔天的恨意,才能支撑着她这具破败的身体不至于彻底崩溃。她猛地又挣扎着要坐起来,气息急促:“我不能躺在这里!我要下去!我要亲眼看着爸爸给我做主,我要亲自看着他怎么死!”
苏文金看着女儿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,心肝俱碎,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,这个从小宠到大的女儿又遭遇了如此可怕的事情。
可是眼下并非伤感的时候,她叹了口气,用力将唐怡重新按回枕头上,语气变得异常严肃:“囡囡,冷静点听妈妈说。你现在躺在这里,报仇还有一线希望!你要是真不管不顾地冲下去闹,把你爸那点愧疚和心疼闹没了,那才是如了他的意,真正放了他一马。你明不明白?”
唐怡猛地僵住,像是被无形的手扼住了喉咙,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,死死盯着母亲:“放他一马?妈,你到底在说什么,我被他害成这个样子……爸怎么会放过他?怎么可能!”她紧紧盯着母亲的脸,无法理解,也无法接受。
难道她的清白、她的健康、她的人生,在父亲眼里,也是可以拿来权衡和交换的吗?
***
楼下,餐厅。
花梨木的古典餐桌上,摆着几样清淡精致的早点:一小碗酱香四溢的炸酱面,码子堆得冒尖,令人食指大动;一盅熬出了厚厚米油的小米粥,点缀着几片脆糯的百合瓣;一笼晶莹剔透能看到里面粉红虾仁的虾饺,还有几碟脆嫩的开胃小菜。
唐振天坐在下首位置,却毫无食欲,手里的银匙无意识地反复搅动着碗里已经微凉的豆浆,他的内心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平静,目光时不时地飘向大门方向,仿佛能看到院子里那个跪着的身影,又小心翼翼地觑一眼主位上不动如山的父亲。
唐部长端坐主位,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老花镜,全神贯注地地吃着面前那碗炸酱面,每一根面条都均匀地裹上酱汁,搭配着黄瓜丝豆芽等面码,送入口中,细细咀嚼,仿佛是什么玉盘珍馐。窗外院子里正上演的负荆请罪戏码似乎与他毫无干系,只是一出无关紧要的背景噪音。
终于,他风卷残云般吸溜完了最后一根面条,连碗底那点浓郁的酱汁都用一片干净的生菜叶擦得干干净净。他放下碗,拒绝了旁边佣人低声询问是否再加一小碗的请求。然后拿起调羹,舀起一勺温度恰到好处的百合小米粥,送入嘴里,细细品味后缓缓咽下。从刚才吃面时的略带豪放,到此刻喝粥的从容不迫,整个转换过程流畅自然,毫无违和感。
做完这一切,他才开口,声音平稳得像是在谈论饭前刚看过的内参消息。
“他动手之前,跟你透过风没有?”
唐振天瞬间头皮发麻,握着勺子的手指下意识地收紧,他知道父亲问的是陈汉升对唐怡下死手的事。他低下头,目光游移,声音因为心虚而不自觉地压低:“他前些天倒是跟我提过一嘴,我当时只当他是被小怡压得太狠了,发发牢骚,就……就随口应了句‘你看着办’。谁承想他,他竟用如此毒辣的手段……”他的声音越说越小,到最后几乎微不可闻。
唐世渊轻轻叹了口气,那叹息声里听不出是失望还是别的什么情绪。他依旧没有看儿子,目光落在面前的粥碗里:“再怎么说,她也是你的亲妹妹。”
唐振天嘴上不敢反驳,心里却翻腾起鄙夷和不屑:亲妹妹?又不是一个妈肚子里爬出来的。更何况,前段时间这个亲妹妹还和陈汉升那个外人眉来眼去,暗中勾结,盘算着怎么把他这个大哥拉下马,好占取唐家的资源和影响力呢。
没跟他们计较就算是他这个大哥厚道了,现在好了,狗咬狗一嘴毛,内部自己打起来了,还打得这么惨烈,难道还要他这个受害者上赶着去劝架不成?他巴不得看热闹!
唐部长似乎能洞悉长子内心那些上不得台面的算计。他没有在兄妹之情这个虚伪的话题上继续纠缠,而是话锋陡然一转,落到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话题,语气依旧平淡得像是在询问一件家常事:“你外面安置的那个,唱程派青衣的小姑娘,叫什么兰的,还有叁个月就该生了吧?”
唐振天手里的银匙“当啷”一声掉进瓷碗里,落在黑色羊绒衫上,留下醒目的白点。但他浑然不觉,整个人如遭雷击,心中已经翻起惊涛骇浪。他自诩风流才子,红颜知己无数,可惜原配夫人只生了两个丫头,在他看来压根不顶用,终究是别人家的人。玩了小半辈子,只有这个科班出身的小花旦肚子最争气,竟然真怀上了,私下找权威专家看了,再叁确认是个带把儿的!这小花旦模样身段唱腔都极出色,带出去也倍儿有面子。喜得他立刻回家打发了原配,火速领了证,就等着孩子落地,风风光光办一场婚礼,好让圈里人都知道他唐振天也有后了,唐家能继承香火了!
他自以为此事做得隐秘,连唐怡都未必清楚细节,父亲日理万机,怎么会知道得如此清楚?连预产期都了如指掌?
他吓得冷汗涔涔,张着嘴,喉咙发干,一句辩解的话都吐不出来。
只听唐部长用安排今晚菜单一样平常的口吻,继续说道:“等孩子生了,就抱过来。给你妹妹养着。她如今这般光景,身边有个孩子,也是个寄托。省得整天胡思乱想,惹是生非。”
轻飘飘一句话,砸得唐振天头晕眼花,脸色霎时惨白如纸。把他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的儿子,他未来所有的指望和香火,抱给那个跟他根本不是一条心的唐怡养?这简直比直接拿刀捅他还让他难以接受,这等于绝了他的后啊!
说到底,唐怡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子,仗着后娘的势,被惯得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都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,父亲这心不知偏到哪里去了!难道就因为苏文金天天吹枕头风?
“爸!这……这恐怕不妥!”他难得强硬了一回,猛地站起身,因为激动,声音都变了调,想要争辩,想要反抗这种安排。
唐部长抬起眼皮,淡淡地扫了他一眼。那目光并不如何锐利,却瞬间将唐振天所有涌到嘴边的抗议和不满都压垮碾碎,只剩下无边的恐惧和驯服。他死死咬住后槽牙,颓然坐回椅子上,低下头,却再也不敢发出半点异议的声音。
这不是商量,这是命令。
“陈汉升能屈能伸,伏低做小这么多年,倒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,不声不响地搭上了林家那条线,攀上了高枝。不得不说,是有点能耐和运道的。这份隐忍和钻营,倒是小瞧他了。”唐部长的语气里甚至带上了些许赞赏。
无论唐振天内心如何愤怒咆哮,父亲这句话已然点明了现实:现在的陈汉升,借着林家的势,确实动不得了。至少,明面上不能轻易动。为了唐家的整体利益,牺牲一个女儿的幸福,都是可以接受的代价。
想到楼上奄奄一息的女儿,又想到身边默默垂泪的妻子苏文金,那颗在权力场中磨砺得坚硬的心中,终究还是难以避免地泛起酸涩,那是一个父亲对女儿残存的恻隐之情,毕竟是从小宠到大的女儿,哪怕她任性妄为。
舐犊情深,哪有父亲不爱孩子,手心手背都是肉,做哥哥的怎么就不懂呢。
唐部长不再看不成器的长子,拿起雪白的餐巾擦了擦嘴角,站起身,朝餐厅门口走去。
这微不足道的情感,在他迈出大门时,瞬间便蒸发得无影无踪。
看到院子里那个虽然跪着,却脊背挺直的陈汉升时,心底那杆衡量得失的天平,毫无悬念地倒向了现实一边。
唐部长的脸上迅速浮现出无奈与歉然的慈祥笑容,仿佛刚刚得知有人在此久跪。他加快脚步走下台阶,亲自伸手去搀扶陈汉升。
“汉升啊!快起来,快起来!这像什么话!地上这么凉,跪久了伤膝盖,落下病根可是一辈子的事!”他用力托住陈汉升的手臂,语气亲切温和,充满了长辈的关怀与体贴,“唉,说起来,都是我疏于管教,把小怡惯坏了,脾气任性又不晓事,往日里让你受了不少委屈。如今闹出这等事,更是……唉,你不计较,还肯来看她,我心里很是欣慰。”
陈汉升脸上那副镇定乃至桀骜的面具,瞬间无缝切换成受宠若惊和沉痛的自责。他就着唐部长的手站起身,膝盖因长时间压迫和寒冷确实传来一阵刺骨的酸麻疼痛,但他身形晃都未晃一下,反而就势微微躬身,姿态放得极低:“爸爸!您千万别这么说!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!是我没用,是我没有保护好小怡,才让她……才让她在外面遭了这么大的罪,吃了这样的苦头……我枉为男人!我对不起您二老的信任,我该跪着。”他声音哽咽,眼圈发红,情真意切得令人动容,仿佛唐怡出事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。
唐部长心中冷笑连连,面上却愈发和蔼可亲,他用力拍了拍陈汉升的手臂,语气变得郑重而诚恳:“好事多磨,好事多磨啊!等小怡把身体养得好一些,你们的婚事也拖了这么久了,终究是件大事,不能再耽搁了。我看,是时候该正式操办起来了,总要给你,也给关心我们唐家的各方一个交代。”这个“各方”,显然意有所指,包括周老板和背后的林家。
陈汉升这一次是结结实实地愣住了,他甚至忘记了继续表演悲痛,猛地抬起头,看向唐部长,眼神里充满了毫无掩饰的震惊与错愕。
这老狐狸非但不找他的麻烦,反而主动提出要完婚?这突如其来的让步,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和代价,让他一时之间有些难以置信。
尽管唐怡现在已成残花败柳,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,但她的身份价值并未完全消失。她是唐世渊正儿八经的婚生女儿,是有着官方背景的千金小姐。对陈汉升而言,就算只是娶一个牌位回去,这门亲事对他而言也是稳赚不赔的巨大胜利。这等于是一张无比光鲜的护身符,一个正式踏入这个核心圈层的通行证。更何况,唐怡现在还活着,这桩婚姻在形式上依然是圆满的。
巨大的狂喜和野心瞬间淹没了最初的惊诧,他几乎是本能地噗通一声,再次跪倒在地这一次带着七分真情叁分演戏,激动地声音发颤:“谢谢爸!谢谢爸的成全!您放心!我陈汉升在此对天发誓,此生必定好好对待小怡,绝不再让她受一丝一毫的委屈!否则天打雷劈,不得好死!”誓言发得又毒又狠,反正他从不信这些。
“好了好了,快起来,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”唐世渊脸上堆满慈祥的笑容,再次亲手将他扶起,甚至颇为自然地任由陈汉升殷勤地搀扶住自己的手臂,“还没用早饭吧?走,进去一起吃点,尝尝你妈特意让人熬的百合粥,驱寒补气的。”
一老一少,一副翁婿和睦的温馨画面,在楼上唐怡难以置信的目光注视下,步履平稳地走进了唐家的大门。
门缓缓合拢,将所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阴谋与算计,都严严实实地关在了这座大院之内。
然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,这不是结束,这仅仅是另一场战争的开端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