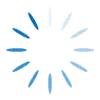这天,夜色像浓稠的墨,泼满了整个城市。
秦奕洲回到家时,玄关的感应灯“啪”地亮起,照出他一脸的疲惫。他松了松领带,将公文包随手放在鞋柜上。连轴转了半个月,今天终于结了一个案子,脑子里那根紧绷的弦骤然松懈下来,只剩下无边的空洞和倦意。
客厅里没开大灯,只有电视机屏幕闪烁着幽幽的光,照亮了沙发一角。
秦玉桐蜷在沙发上,身上盖着一条薄毯,怀里抱着个抱枕,电视里放着最火的电视剧《仙剑奇侠传三》。
听到动静,她回过头,“爸爸,你回来啦。”
清甜的嗓音驱散了满室的清冷。
秦奕洲“嗯”了一声,换鞋的动作有些僵硬。他发现自己现在有点怕这种只有他们两个人的独处空间。
就在他准备说句“早点睡”就回屋时,秦玉桐却从沙发上跳了下来,光着脚跑到他面前。
“等一下哦。”
她像只小兔子,一溜烟钻进了漆黑的厨房。几秒后,黑暗中亮起了一点豆大的、温暖的橙光。
她捧着一个小小的蛋糕走出来,蛋糕不大,也就四寸,上面插着一根孤零零的蜡烛。烛火摇曳,映在她清澈的眼眸里,像落进了两捧碎钻。
“生日快乐,爸爸。”
她仰着脸,笑意盈盈地看着他,“你都忘了吧?三十三岁啦。”
秦奕洲彻底愣住了。
是啊,今天是他生日。
一个连他自己都忘得一干二净的日子。
她是他亲手养大的女孩,是他法律上的女儿,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。
可他,却对这束光,生出了最肮脏、最不可告人的念头。
“怎么不说话呀?”秦玉桐歪了歪头,举着蛋糕的手有点酸了,“快许个愿,然后吹蜡烛。”
秦奕洲看着她眼里的光,那光太干净,干净到能照出他灵魂深处所有的龌龊和不堪。
他缓缓抬起手,却不是去接蛋糕。
指尖,隔着半寸的空气,描摹着她脸颊的轮廓,眼神晦暗不明。
“小乖,”似是难以启齿,“我的愿望……如果说出来,会吓到你。”
烛火在秦玉桐的瞳孔里跳跃,像两簇烧得正旺的野火。她没被秦奕洲那句暧昧不明的话吓退,反而笑得更甜,露出一口细白的糯米牙。
“有什么愿望会吓到我呀?”她歪着头,声音娇憨,“是想一夜暴富,买下整个津市,还是想毁灭地球,当宇宙大魔王?”
她用最孩子气的玩笑,轻轻巧巧地,就把他话里那份沉重到快要溢出来的危险情愫给化解了。
秦奕洲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。他看着她,仿佛在看一个披着纯洁外衣的妖精。她什么都懂,又好像什么都不懂。
他猛地俯身,一口气吹灭了那根蜡烛。
“啪。”
火光熄灭,只剩下电视屏幕的光,在两人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剪影。空气里只剩下一缕淡淡的青烟,混着奶油的甜腻味。
“不许胡闹,”他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沉稳,甚至可以说是冷硬,“时间不早了,去睡觉。”
说完,他转身走向吧台,背影挺直,像一棵雪中的松。拉开酒柜的门,拿出一瓶威士忌和一只古典杯,冰块撞击杯壁,发出清脆又寂寞的响声。琥珀色的酒液被注入杯中。
秦玉桐没动。她光着脚,踩在冰凉的木地板上,像一只潜伏在暗处的猫,无声无息地跟了过去。
“爸爸,”她凑到他身后,鼻尖几乎要碰到宽阔的后背,贪婪地吸了一口他染上浓郁酒气的味道,“你在喝什么?好香。”
秦奕洲的身体瞬间绷紧了。他没有回头,只是端起酒杯,仰头喝了一大口,辛辣的液体灼烧着他的喉咙,却浇不灭心里的那团火。
“小孩子不该问。”他声音沙哑。
“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”秦玉桐不依不饶地绕到他面前,指尖点了一下他手中的玻璃杯,冰凉的触感让她缩了缩手,“我明年就十八岁了,是大人了。你就让我尝一口,好不好嘛,爸爸?”
她拉长了尾音,软软地撒着娇。这是她百试不爽的武器。
秦奕洲垂眼看着她。女孩的脸颊在电视变幻的光线下,白得像瓷,一双眼睛水汪汪的,写满了好奇和央求。他知道自己该拒绝,该立刻把她赶回房间,锁上门。
就在他失神的这一秒,秦玉桐眼疾手快,一把抢过了他手里的杯子。
“我就尝一小口!”
她学着他的样子,仰起天鹅般优美的脖颈,将杯里剩下的酒一饮而尽。
“咳……咳咳!”
辛辣的液体毫无准备地冲进喉咙,呛得她惊天动地地咳嗽起来,眼泪瞬间就涌了上来,一张小脸涨得通红。
“胡闹!”秦奕洲脸色一变,终于有了真实的怒气。他夺下空杯,重重地放在吧台上,一手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体,另一只手拍着她的背。
她怎么这么瘦?从前的肉都去哪了?
酒劲上得很快,秦玉桐只觉得天旋地转,整个世界都晃了起来。客厅里的电视机变成了模糊的光团,秦奕洲的脸就在眼前,那么近,近到她能看清他金丝眼镜下,那双狭长狐狸眼里翻涌的震惊、懊恼,还有……一丝深不见底的欲望。
所有被压抑的情绪,都在酒精的催化下,破土而出。
她不咳了,只是抬起一双水汽氤氲的眼,痴痴地看着他。
“秦奕洲……”她忽然开口,叫了他的全名。
“你的愿望……”她踮起脚尖,柔软的身体毫无保留地贴了上去,温热的呼吸喷在他的下巴上,带着威士忌的酒香和她独有的甜香,“……是不是我?”
男人呼吸骤然粗重,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,女孩温软的唇,就笨拙又急切地堵了上来。
那是一个完全没有技巧的吻,带着孤注一掷的莽撞。她的牙齿甚至磕到了他的嘴唇,传来一丝微弱的刺痛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