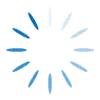津市的天气预报说,未来一周都是晴天,秋老虎去而复返,气温会回升到让人冒汗的程度。
可秦玉桐觉得,那场大雨,就没停过。
它一直在下,灌进她的耳朵,蒙住她的眼睛,浸透她的骨头缝,让她从里到外都泛着一股湿冷刺骨的寒意。
她病了,高烧反反复复,一连三天都下不了床。
秦奕洲推掉了所有不必要的应酬和会议,甚至把一些卷宗带回了家,寸步不离地守着她。
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和中药混合的味道。
秦玉桐蜷在柔软的被子里,只露出一张烧得通红的小脸,嘴唇干裂起皮,长而卷的睫毛湿漉漉地黏在一起,像两把破损的蝶翼。
她攥着那枚带血的耳钉,攥得死紧。
“叩叩——”
门被轻轻敲了两下。
秦奕洲端着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走进来,脚步放得极轻。他只着了件柔软的灰色羊绒衫,金丝眼镜下的那双狭长狐狸眼,褪去了法庭上的锐利,只剩下沉静的担忧。
他走到床边,在床沿坐下,伸手探了探她额头的温度。
“还是烫。”他蹙了蹙眉,声音低沉。
他用勺子舀起一勺粥,送到唇边吹了吹,试了试温度,才递到她嘴边。
“小乖,吃点东西。”
秦玉桐没什么反应,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上繁复的石膏线,仿佛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娃娃。
秦奕洲也不催,就那么耐心地举着勺子。
温热的米香,丝丝缕缕地钻进鼻腔。
过了许久,秦玉桐才缓缓转过头,机械地张开嘴,将那口粥咽了下去。
温热的食物滑过喉咙,却暖不进早已冰凉的胃。
他就这样,一口一口地喂着。
一碗粥见了底,秦玉桐的额头上也冒出了一层细密的虚汗。
秦奕洲放下碗,抽了张纸巾,俯身过去,仔仔细细地替她擦掉唇边的米渍。
他的指腹温热干燥,带着一股好闻的香草味道,不经意地擦过她的唇角。
眼泪毫无预兆地,就这么滚了下来。
“爸爸……”她的声音嘶哑,“我是不是很脏?”
秦奕洲擦拭的动作一顿。
他抬起眼,透过薄薄的镜片,静静地看着她。
那目光深邃,像一口古井。
“为什么这么说?”
“江临……他不要我了。”秦玉桐的身体开始发抖,像是被丢在冰天雪地里,“他觉得我背叛了他……他把戒指扔了……扔进江里了……”
她的话说得颠三倒四,毫无逻辑,可秦奕洲听懂了。
“是我不好,”她的眼泪流得更凶,哽咽着,几乎喘不上气,“都是我的错,如果我没有去瑞士,如果我离陆朝远一点……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发生?”
她像个溺水的人,语无伦次地剖白着自己,每一个字都带着血。
把所有的罪责,都揽到自己身上。
秦奕洲没有说话。
他只是沉默地听着,任由她把所有的委屈、悔恨和绝望都倾泻出来。
等到她的哭声渐渐变小,只剩下压抑的抽泣时,他才伸出长臂,将她连人带被,一把捞进了怀里。
秦玉桐把脸埋在他的胸口,贪婪地汲取着那份独属于他的气息。她能清晰地听到他胸膛下,那沉稳有力的心跳声。
“咚——咚——咚——”
像寺庙里悠远的钟声,一点一点,抚平了她内心的狂躁与惊惶。
“不是你的错。”秦奕洲笃定。
他一手揽着她颤抖的脊背,一手轻轻抚摸着她汗湿的头发。
这五个字,仿佛一道神谕。
秦玉桐埋在他怀里,像只找到了巢穴的幼兽,身体的颤抖渐渐平息。
“可是……”她哽咽着,还想说什么,却被秦奕洲打断了。
他稍稍松开她一点,垂下那双狭长的狐狸眼,透过金丝镜片的边缘,落在她湿润的眼。
“小乖,”他叫她的小名,声音里带着一种奇特的冷静与温和,“人不是植物,不能只靠一片土壤活着。当阳光不够,雨水不足的时候,藤蔓会本能地朝有光有水的地方蔓延,这是求生的本能,不是背叛。”
秦玉桐怔住了,呆呆地看着他。
她从未听过这样的论调。在她的世界,或者说所有人都认为,爱是忠贞,是唯一,是划地为牢。
秦奕洲的指腹轻轻摩挲着她的单薄背脊。
“江临给不了你足够的安全感,所以你会在陆朝身上寻求庇护。你觉得冷,所以会下意识靠近另一处火源。这无关对错,也无关脏不脏。”
“他不爱你,是他的损失,不是你的失败。这个世界上,能给你爱的,不止只有一个。”
他顿了顿,镜片后的目光深邃得像一汪寒潭,“你的道德感太高了,高到像一把枷锁,把自己锁在里面,动弹不得,还以为是自己的罪过。”
这番话,如同平地惊雷,在她混沌的脑海里炸开。
道德感……太高了?
一直以来被奉为圭臬的东西,在爸爸的口中,竟然成了一把枷锁。
房间里只开了一盏昏黄的床头灯,光线将秦奕洲的轮廓勾勒得模糊又温柔。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像在拥抱她。
那张平日里只用来签署文件、敲击键盘的手,正以一种安抚的姿态,一下一下,有节奏地拍着她的后背。
仿佛在为他刚刚那番离经叛道的言论,落下最权威的印章。
“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。”他俯下身,“不用害怕,不用顾忌。去疯,去闹,去把所有你想要的都抢回来。”
“爸爸给你兜底。”
这最后一句话,轻飘飘的,却比任何承诺都重。
它像是一张空白的支票,一张无限的通行证。
它告诉她,她可以推倒这个世界所有的规则,因为身后,永远有他。
秦玉桐的眼泪,再一次汹涌而出。
但这一次,不再是因为痛苦和自责。
她抬起头,那双被泪水洗过的眼睛,在昏暗的光线像两颗浸在水里的黑曜石。她怔怔地望着他,望着这张近在咫尺,骨骼深邃的脸。
他清冷禁欲,是法庭上言辞犀利的检察官,是所有人眼中克己复礼的秦先生。
可现在,他却在教她离经叛道。
一股荒唐又疯狂的念头,毫无征兆地从心底最深处破土而出,像藤蔓一样,瞬间缠绕住她所有的理智。
她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,带着一丝试探与渴求。
“那……”
秦玉桐舔了舔干裂的嘴唇,鼓足了所有的勇气,轻声问:
“……我想和爸爸在一起,也可以吗?”
空气,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。
床头灯的光晕,似乎都停滞在尘埃里。
秦奕洲揽着她脊背的手,几不可查地僵了一下。
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,但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,瞳孔却骤然紧缩。
怀里的小姑娘,正用一种全然信赖、又带着点孤注一掷的眼神望着他。那眼神太纯粹,太干净,像初生的麋鹿,义无反顾地撞进了他内心最幽暗的森林。
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喉结不受控制地滚动了一下。
他怕。
怕自己再多看一秒,就会将那些压抑了十几年,早已扭曲变形的欲望,尽数释放出来。
更怕她此刻只是高烧下的胡言乱语。任何一个不恰当的回应,都可能将她推向更深的深渊。
几秒钟的沉默,漫长得像一个世纪。
最终,秦奕洲缓缓松开了她,指尖却转而探向她的额头,用手背贴了贴。
这个动作自然而然,巧妙地拉开了危险的距离。
“烧得更厉害了。”
他的声音恢复了之前的沉稳,听不出任何波澜,“连胡话都说出来了。”
他没有回答“可以”,也没有回答“不可以”。
只是用一个父亲对生病女儿的担忧,轻描淡写地,将那个足以引爆一切的问题,化解于无形。
秦玉桐看着他,看着他重新为她掖好被角,看着他起身去拿温水和退烧药。他宽阔的背影挺拔如松,每一个动作都从容不迫,仿佛刚才那个石破天惊的问题,真的只是一句无足轻重的梦呓。
巨大的失落和疲惫感席卷而来,她再也支撑不住,眼皮一沉,坠入了黑暗的睡梦里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