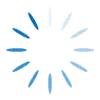一年没回家,说一点不想念是假的。
任知昭想她的小房间,想安大略湖,想海莉。
当然,也会想妈妈。很没出息,但她也没办法。
有些人,就是只适合远远地想,不适合近距离端详。诚然想念,但任知昭不愿意回家住。
动身前,她考虑过在多伦多租房。后来想想,还是算了。
她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,是上夏校,多修学分,争取提前毕业。她清楚以后时间只会越来越少,趁现在必须快马加鞭完成学业。因此,她也待不了多久,与其把钱砸在租房上,不如拿去吃好玩好,犒劳自己。
至于市中心那套离学校近,条件理想,她曾住过的房子……她不考虑。
结果前脚刚进家门,她就后悔了。
一年未见的斯卡布罗,以高分贝的一嗓子欢迎她归来:“你怎么晒成这个死样,你看你那胳膊都黑成啥了!”
任子铮跟在她后面进门,分担了点火力,得到了“哟,这是哪位稀客?”和“你还知道回家?”之类的问候。但几句过后,炮口很快又转回任知昭一个人身上。
任知昭表情淡然,对朝她而来的唇枪舌剑全盘接收——
“我怎么了,我觉得我……挺好看的啊……”
“美国咋了,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?”
“我是独立音乐人,没那么夸张好吗。”
“……没人潜规则我。”
“噗——保什么镖,你可真能想,不至于。”
“没人会骚扰你的,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”
任子铮大概是看不下去了,突然横插一脚,搭住王桦的肩:“妈,你上次不是问我美元资产配置的事吗,我整理了点数据给你看看呗——”
“你一边儿去。”王桦看都不看他,“什么叫我把自己当回事啊——”
任知昭当然早有心理准备,但真对上这一轮火力,心里仍生出压迫感。
她懒得再开口,索性甩手出门,屁股都没坐热,留王桦在身后叫:“你去哪儿?刚回来就走!家里是宾馆吗!”。
眼不见,耳不听,心就不烦了。这是任知昭日渐成熟的技能。
出了门,没地方去,她干脆去海莉家。拐叁个街角就到,不远的,从前放学后为了不回家,她常去。
一年未见的老友,照面时只是一个拥抱,无须多言。两叁句闲聊,就填补了一年的空白。四五句话之后,短途出游的计划便定下,不必等,即刻出发。
安省的五月没有加州那么热浪汹涌。春意尚存,是最舒服的季节。
海莉选的目的地,任知昭来过。上次来是冬天,漫天飞雪。这一次,她见到晚春初夏的马斯科卡。
她们订了间木屋,比冬天那次要小,两个人住正好。位置依旧临湖,被繁茂的树木环抱。
空气是墨绿色的,潮湿的木质气息从湖面漫过来,在肺叶上洇开。任知昭趴在躺椅上,闭着眼,身心浸入湖畔的薄雾。阳光不多不少地洒在背上,耳边,海莉的声音叽叽喳喳地响。
“——一人包揽作曲,作词,编曲,录制,独立完成了首张专辑的制作。今年夏天,她带着录音室重制版回归,歌曲迅速席卷榜单。正如 Pitchfork 所评价:‘这是一股夏夜海岸线上涌来的Y2K浪潮。’”
海莉漫不经心地在任知昭背上抹开防晒霜,注意力却全在手机屏幕上,故意把文字念得很大声,
“菲比,来自加拿大的二十岁天才唱作人,出生于中国上海一个音乐世家,自幼便展露出惊人——”
“哎呀行了行了行了。”
任知昭忍无可忍,抬起胳膊打断她声情并茂的朗诵。那些添油加醋的文字,是经纪公司安排的第一个采访,现在当事人心情就是十分后悔。
“什么音乐世家……什么天才……真能扯淡。”
她现在不喜欢“天才”这个词了。轻描淡写,就把熬了无数个日夜的血泪抹去。吃那么多苦,算哪门子天才。
海莉笑了,低头凑近她,语气神秘兮兮:“你有没有想过,你为啥过得那么疯狂?”
任知昭扭过头看她。
海莉耸耸肩:“因为天才就是会有些疯疯癫癫的。”
这话说的,任知昭一个翻身坐起:“Excuse me,我哪里疯疯癫癫了?我现在可正常,可健康了好吧。”
“噢?怎么个健康法呀?”海莉笑眯眯靠回到躺椅。
“你知道我多久没碰这玩意儿了吗?”任知昭指了指海莉手边放的香槟,“我现在连饮料都不敢乱喝,每天就吃草,做有氧,做瑜伽,冥想。”
“哇,恭喜你,穷尽一生变成白女啦!”
“滚。”
海莉继续托腮看着她笑,笑得任知昭发毛:“你干嘛……”
“我在想,那天数学课,还好我一眼看中了看上去不好惹的你,坐到你身边,不然现在哪能在这儿享受富婆买单的美景美酒呀~”
任知昭也扬了嘴角,伸手把额上的墨镜滑到眼睛上:“叁千加币一个人,回头转给我。”
“咱俩谁跟谁呀,谈钱伤感情~”
海莉拿起酒杯灌了一大口,对着湖面长舒一口气。
“诶,咱俩今晚还接着躺吗?要不搞点刺激的,去镇上蹦迪,或者点两个男模来家里玩玩?”
任知昭轻轻拉下墨镜一角,让对方看清自己的白眼。
“好好好,我错了,忘了你已经心有所属,身有所属了~”
“谁身有所——谁——”任知昭差点从躺椅上蹦起来,“把你踹湖里去信不信!”
“哎呀跟我就别嘴硬啦,就该把你昨晚那死样录下来,以后你一嘴硬就放给你听你说的那些话。”
“我说什么了我!”
任知昭回忆起月黑风高的昨夜。老友相聚,分外激动,难得喝酒。两杯下肚,她就都招了,把自己在山里“辟谷”的故事删掉少儿不宜的部分全盘托出。后来两杯又两杯,那些删减部分也被她交代干净,讲得那叫一个声泪俱下,听得海莉是瞳孔地震,二人抱头痛哭……
任知昭痛苦地捂住额头,发誓此生与酒精不共戴天。
“哎,我都有点嗑你们了,一对神经病,绝配呀。”海莉啧啧几下,话里带笑,“你俩谁流通到市场上都是霍霍人,真的不在一起吗?”
任知昭没有回答。
她垂眸,看见肚脐周围的绒毛,在阳光下泛着微弱的金光。
她的每一根毛发,每一寸皮肤,都跟着她吃了很多苦。它们是那样生动而脆弱,她理应好好守护,不再叫它们受苦。
片刻安静后,海莉再次开口,声音沉了下去:“菲比,这世上任何极致的东西都是罕见的,极致的爱也是。你有没有想过,也许你天生就是这么极端的人,你的人生,本来就需要疯狂又病态的爱呢?”
任知昭平静地抬眼,不置可否。
最开始,她享受精心设计的堕落游戏,看清白染上污浊,享受所有为她而流的泪。后来,她把自己搭进去。近乎自毁的狂热像毒瘾,痛苦,戒不掉。
你也一样,是吗?所以我们互相吸引,哪怕彼此毁灭。
她托着下巴,声音很轻:“相爱的人不一定要在一起的。”
爱的悖论在于,它既能跨越最不可能的鸿沟,又会在看似微不足道的裂缝中溃败。
几只蓝鹭贴着水面拍翅而过,留下叫声回荡。她隐约听到海莉玩味又轻蔑的一声:“Bullshit~”
任知昭望着湖面,潮湿沉郁的气息仍黏在鼻腔里。
是雪松林。陈年树脂混着霜雪的味道,曾裹住她十八岁狂跳的心脏。她记得。
她闭上眼,雪松,大雪,他的围巾……
睁开时,却只有晴空。风很轻,阳光从树隙间簌簌跌落。
想给他打电话,告诉他天气晴朗,阳光和那个初冬的午后一样好。
偶尔,任知昭会这样暂停,闭眼,只为更清晰地想念。
但再睁眼,她也只会让心中所想沉进暮色,与那阳光一起。
阳光再出现时,行李已立在门边。海莉正对着镜子理头发。
“菲比。”她突然转身,“我在尼皮辛有些朋友,临时约我过去玩两天。”
任知昭拉背包拉链的手一顿:“所以?”
“所以我就不跟你回去啦。”
“你要把我一个人撇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?” 任知昭一下撂下包,直起身。
她们可是开着海莉的车来的!
“怎么会。”
海莉“噗”地笑了。窗外传来汽车碾过碎石的声响,由远及近。
“有人来接你呀。”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