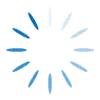亥时已过,殡仪馆门前人群渐稀,只余满地狼藉的花牌挽联和空气中尚未散尽的香烛余味。
陆续送走几位好友,齐诗允在雷耀扬陪同下走出大门。
她低着头,折成叁角的粗布头巾遮住了脸上的表情,而那死死扣住盒缘、紧绷到发白的指节,泄露了她内心近乎偏执的坚持。
她怀中紧紧抱着那个沉甸甸的、冰凉的黑檀木骨灰盒,抱着方佩兰留给她的、在这世间唯一的余温。
风水师站在一旁,低声建议尽早择吉日让逝者入土为安,而她却像是没听见,站在原地一动不动,就像是要与怀中的阿妈永远粘合在一起。
雷耀扬侧头,见她这副模样,心如刀绞。
他知道,一旦下葬,就意味着真正的、物理上的永别…这对本就无法接受现状的她,实在过于残忍。
他需要给她时间,哪怕只是短暂的缓冲。他不能再逼她了。
男人深吸一口气,强压心中酸楚,对风水师摆了摆手:
“劳驾大师再多看几个地方,烦请挑个最稳阵、最好的吉时,不急。”
再回到半山时,已快凌晨。
这个曾经充满温馨与生活气息的家,此刻却像一座华丽封冻的坟墓,每一个角落,都弥散着让人透不过气的悲伤。
空气里,似乎还残留着方佩兰煲汤的香味,耳边,似乎还能听到她带着笑意的唠叨……
齐诗允一路沉默着,径直走向阿妈生前暂住的房间,站在房门口愣神。
房间收拾得整洁有序,仿佛主人只是暂时出门,不多久就会归家一样。
床头柜面,还放着方佩兰睡前会看的菜谱,开放式衣橱里,挂着她常穿的几件舒适棉衫,梳妆台上,那瓶她用惯多年的、味道熟悉的雪花膏还静静地立在那里。
一切都维持原貌。唯独人,不在了。
女人迈步走入,痴痴地站在房间中央,略显呆滞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件遗物。最终,视线落在床头那张由陈家乐影下的、多年前她和阿妈在深水埗家中的合照上。请记住网址不迷路poshu8.com
照片里,母女俩头靠着头,笑容无比灿烂。
那时虽然清贫,却拥有着最朴实的温暖和幸福。
而不久前,就在这个房间里,方佩兰还拉着她的手,温柔却坚定地说着要搬回旺角,让她和雷耀扬有多些二人世界…当时她还跳脚反驳,撒娇耍赖…那些对话言犹在耳,温热的触感仿佛还停留在指尖……
怎么会…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样?
巨大的不真实感和绝望,再次将她吞没。
她缓缓蹲下身,抱住那个冰冷的骨灰盒,将脸颊贴在上面,仿佛这样…就能感受到阿妈没有离她而去的温度。
一行泪水顺着脸颊无声滑落,浸湿了光滑的木盒表面。
她没有哭出声,只有肩膀小幅度地颤抖着,在竭力把所有情绪都压缩到极致。
雷耀扬几通电话处理完一些后续事宜,走上楼,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幅景象。
他的齐诗允,独自蜷缩在方佩兰生前住过的房间里,抱着那骨灰盒抽泣……整个家,在一夜之间变得七零八落残缺不全,悲恸再度涌上心头,几乎要将他击碎。
男人站在门口,脚步沉重如灌铅,无法迈入。
他很想上前抱住她,想告诉她,还有他在…想安慰她说,一切都会过去…可是,所有的话语,在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。
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「意外」,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,无法接受!
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和自我厌弃袭上心头,他痛恨自己的身份,痛恨自己背后所代表的黑暗与危险,还有那些不可告人的家族和父辈的秘密……
如果不是他,方佩兰此刻应该正在家里,等着女儿回来吃饭…而不是变成一捧冰冷的灰,被齐诗允如此绝望地抱在怀里。
是他,将灾难和死亡带给了这个原本温暖平静的家,让他最心爱的女人,后半生都要活在这无尽的痛苦与阴影之下……
这些想法像一把利刃,将他千刀万剐,他甚至觉得,自己连安慰的资格都快要失去。
望着齐诗允那封闭的、完全沉浸在自身悲痛中的背影,他感觉到两人之间那层无形的、冰冷的隔阂已经变得越来越厚。
这段他无比珍视、以为坚不可摧的婚姻,在经历了种种猜疑、隐瞒、以及这血淋淋的生离死别后,突然变得如同精致却脆弱的玻璃器皿,布满了裂痕,仿佛轻轻一碰,就会彻底碎裂。
而这个曾经象征着爱与归宿的家,此刻也让他感到无比窒息和孤寂。
同时,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疲惫感席卷而来。
那是源自灵魂深处的疲乏,不仅要面对外部的明枪暗箭,还要承受内部这无声的、却更具毁灭性的煎熬。一路来,他已经独自承受太多,却看不到一丝通向未来的曙光。
雷耀扬沉默着,没有走进房间。
因为现在的他,已经说不出任何宽慰的话语,只有站在她身后默默守护。
他靠在门框边,凝视齐诗允的背影许久。
最后,又轻声掉头离开。
夜色渐深,窗外山脚下的璀璨灯火,此刻看来也只像无数冷漠旁观的眼睛。
客房里,齐诗允终是抵不过连日守灵的身心煎熬,抱住冰冷的黑檀木骨灰盒,在方佩兰生前睡过的床上,浑浑噩噩地陷入了不安的浅眠。
须臾过后,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滑入房间。
是Warwick。
平日油光水滑的黑棕色皮毛此刻似乎也黯淡了几分,敏锐的深棕色眼眸失去了往常的机警锐利,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动物特有的、感知到巨大悲伤后的沉静与忧虑。
它慢慢踱到床边,四肢踩在地毯上没有发出任何声音,也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兴奋地摇尾或试图蹭蹭女主人,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,昂头凝视着齐诗允即使在睡梦中依旧痛苦的面容,从喉咙里发出极其轻微的呜咽声。
犹豫了片刻,它选择安静地伏下身,静卧在床边的角落中。将下巴搁在交迭的前爪上,一双忠诚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守护着床上的人。
Warwick的存在,就像一个沉默温暖的守护者,在这冰冷的悲伤之夜里,提供着一丝微弱却坚实的依靠。
没多久,雷耀扬悄无声息地再次推开门。
看到这画面时,他不禁动容。
男人放轻脚步走过去。Warwick立即警觉地抬起头,望清对方面容后,两只耳朵微微动了动,又重新伏下,只是用目光一路追随他。
他下弯腰,小心翼翼地拉起滑落的被角,动作轻柔至极,生怕惊扰了齐诗允短暂而珍贵的睡眠。
雷耀扬凝望对方睡颜,指尖悬在半空,想要抚平她紧蹙的眉心,却只是无力地垂下。
临走前,男人蹲下身,轻轻揉了揉Warwick的脑袋,低声道:
“替我陪住她。”
Warwick仿佛听懂了一般,极轻地嘟囔了一声,舔了舔对方纱布包裹下露出的手指,然后再次将目光投向齐诗允。
沉默地站了片刻,雷耀扬才悄声退出了房间,又轻轻带上了门。
走到楼下客厅,暖黄的灯光晕开一片,忠叔早已等候在一旁,准备好了医药箱。
自从出事后,一连几晚都没睡踏实。老人眼中满是血丝,脸上每一道皱纹刻满了对他担忧与心痛:
“少爷,该换药了。”
闻言,雷耀扬走过去坐下,沉默地伸出手,任由对方一层层解开那早已被血渍和药渍浸透的纱布。
即便这些天已替他换过一次,但想到内里狰狞可怖的伤口时,忠叔的双手还是有些不受控地抖动。
须臾,他颤巍巍地揭下那些纱布。
当那骨节分明、能优雅从容地弹奏莫扎特、也沾满仇敌血腥的双手…露出皮开肉绽、甚至有些扭曲的伤口时,客厅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
“…少爷,我看伤口还是很严重……”
“既然葬礼已经办完,距离下葬也还有段时间,这些天你就不要再劳心劳力了。”
“你好好休息。少奶奶那边,我和佣人会把她照顾好。”
默默听着忠叔一如往常的关心和嘱咐,男人低下头去,宽阔的肩膀难以抑制地微微颤抖起来,从他喉咙里发出压抑的、前所未有的哽咽。
连日来强撑的冷静和镇定,压抑的悲痛和无尽的自责,还有对外追查的种种压力,以及对齐诗允状态的恐慌……所有沉重的负担,在这一刻,在这位看着他长大、如同父亲般的老人面前,终于彻底击溃了他紧绷的神经。
眼下,他不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东英奔雷虎,也不再是那个需要时刻伪装坚强的丈夫。
现在的他,仿佛变回了许多年前那个在雷家大宅里受了委屈,只能躲在房里偷偷哭泣、金尊玉贵却又无比孤独的雷家二少。
“…忠叔…怎么会搞成这样……”
“我…我应承过…会照顾好她们…我……为什么………”
高大男人语不成调,无限茫然与痛苦从周身漫溢出来。
忠叔听得老眼泛红,动作极其轻柔地用蘸了药水的棉签,仔细清理着伤口边缘的血污,每一次颤抖的触碰都小心翼翼,就如同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……
老人看着这双本应抚弄琴键、执掌权柄的手变成如今这般模样,心中的痛惜难以言表。
思考须臾,他微微叹了一口气,声音带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沉静:
“少爷,这不怪你。”
“人活一世…有好多事,是不能随心所欲的……”
“恶人想要做恶…谁都无法预料…况且这次事发突然,你不要把所有错都揽到自己身上。”
“这真的…不怪你。”
他手上动作没停,仔细地涂抹着药水,语重心长说着宽慰的话语:
“齐太离开,大家都好心痛……”
“但少奶奶现在最需要的是你,你一定要撑住。如果连你都垮了…她一个人…怎么办?”
老人的话语像涓涓细流,试图滋润雷耀扬枯竭的心脉。
对方垂下头,闭着眼,泪水向下无声滑落,浸湿了衣襟。只有在忠叔面前,他才能短暂地卸掉所有重担,袒露那份深藏的脆弱与无助。
而楼上,Warwick的无声陪伴,成了这个夜晚,唯一一丝微不足道却真实存在的温暖。
第二日中午,阳光勉强穿透灰霾,却带不来丝毫暖意。
雷耀扬几乎是彻夜未眠,因为每隔一段时间,他就要去客房查看齐诗允的状况。
幸好,她睡得还算安稳,并不像在医院里那样时常惊醒。此刻,他强打着精神在书房处理一些紧急事务,眼底的红血丝更重,但情绪已被重新强行压抑回冰封之下。
须臾,坏脑匆匆进来,脸色凝重中带着一丝突破进展的曙光:
“大佬,有消息。”
“有个当时经过机场高速的货车司机,说撞车后,隐约看到有个男人从泥头车驾驶座爬出来。”
“他好慌张,甚至不顾危险跳过隔离栏,立马跑去对面车道,而且有车接应,好快就离开事发现场。”
听到这里,雷耀扬猛地抬起头,眼中寒光骤现:
“看清个样未?”
“个司机话离得远,加上混乱,只见到个大概。”
“不过他讲那个人好瘦,着深色衫,戴顶帽和口罩。当时根本看不清个样,但肯定…不是差佬公布的那个失踪的原车司机。”
说话间,坏脑递上一张根据目击者描述绘制的模拟画像,但上面的人像五官陌生又模糊,特征并不明显:
“差佬根据这个线索,发布了新的悬赏通缉令,只是不知几时才能有消息。”
话音落下,雷耀扬盯着那模糊的画像,程啸坤的名字却如一道晴天霹雳顿时跃然脑海。
但前段时间,警方给出的那些尸检报告与程啸坤本人高度吻合,他很想要否定这个想法,却又像是被一道无形丝线牵引着,走入了另一片迷雾之中。
男人琢磨着,手指无意识地收紧,伤口被牵扯带来一阵刺痛,却在无比清晰地警醒自己:
“…身型很瘦。”
“保险起见,你再去留意对面车道监控,查下那个时间点有哪些可疑车辆经过。还有,洪兴那边继续盯紧,有任何异动及时通知我。”
坏脑领命后,正要转身,可恰在此时,书房门被轻轻推开。
齐诗允不知何时醒了,神情极其复杂地站在门口。
女人面色惨白,如大病一场,身上还穿着昨天的衣服,宽大的孝服显得她更加瘦弱不堪。而她显然听到了刚才的对话,一双红肿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坏脑,又猛地转向雷耀扬,声音因为紧张和急切而微微发颤:
“坏脑哥!是不是有消息?!是不是找到那个肇事司机?!”
“程啸坤?!”
“是不是他?!”
说着说着,她的情绪瞬间激动起来,呼吸也变得急促,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,又仿佛即将面对更可怕的真相,整个人,都处于一种极度紧绷的状态。
见状,坏脑下意识地看向雷耀扬,并不敢轻易作答。
男人立即起身走过去,扶住她颤抖的肩膀,放柔声音,极力安抚道:
“诗允,你冷静点。”
“只是有目击者见到有人逃离,未确定是谁,差佬已经———”
“目击者?!见到什么?!”
“个样呢?!画出来未啊?!给我看!!!”
显然,此时的齐诗允根本听不进他的话。
她猛地挥开他的手,目光死死锁在坏脑手中那张纸上,情绪激动到失控:
“是他!一定是他!”
“程啸坤他未死!是他返来报仇!是他害死我阿妈!”
“还有那个撞击角度!很可能就是冲着我来的!”
凭借着心中那股不详又强烈的预感,她声嘶力竭地发出指控,虽然雷耀扬极力劝说让她镇定,却也徒劳无功。
而在这强烈刺激下,让女人再次陷入混乱与自我谴责的漩涡,泪水夺眶而出:
“…不……不是…”
“都是我…是我连累阿妈…好端端的……我为什么说要去旅行?如果不是我…阿妈现在一定好好在家…什么事都不会发生……”
“但是阿妈好无辜…她是为了护住我才……”
“……该死的人…是我才对!”
她站在原地喃喃自语,发高烧一样说胡话,雷耀扬眼见她这副模样,仿若万箭穿心却又无能为力。他只能强行将想要挣脱的女人再度拥入怀中,用温和言语安慰着,并快速朝坏脑使了个眼色。
光头佬会意,立即收起桌上的画像,无声地退了出去。
渐渐,书房里,只剩下齐诗允压抑不住的、绝望的痛哭,还有雷耀扬沉重却无力的呼吸声。
真相的迷雾似乎散开了一角,却带来了更深的恐惧与痛苦。
而那张模糊得让人毫无头绪的画像,如同一个鬼魅,悬在他们心头,预示着这场悲剧,远未到落幕的时刻。
不知过了多久,齐诗允激动痛苦的质问声逐渐被绝望的啜泣取代。
雷耀扬紧紧抱着她颤抖不止的身体,感受着她的泪水浸湿自己胸前的衣襟,那滚烫的温度几乎要灼伤他的皮肤,更灼痛他的心。
“不是你的错……”
“…诗允,你千万不要这么想。”
男人一遍遍在她耳边重复,试图驱散她那可怕的自责念头:
“你要怪就怪我…一切都是我的错………”
“是我不好…是我没有足够警惕到那辆车……连累阿妈…也连累你……”
“对不住…真的对不住……”
他痛斥自己,将所有罪责都揽下,愧疚感迫使他将姿态压得极低,语气里也充满了无尽的痛悔。
听到对方这连续不断的道歉,齐诗允抓紧对方衣襟,哭得更加伤心。
如若真的要追根究底,自己才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。她每一刻都在后悔这次假期旅行的安排,如果当时她临时改变主意…该有多好?
但是人生只有一次,根本经不起假设。
情绪又历经一阵起起伏伏,哭声渐渐低了下去。
房中的声音,变成了一种虚脱的抽噎,仿佛所有眼泪和力气都从体内流逝殆尽,只剩一副躯壳。
齐诗允半靠雷耀扬怀里,望着落地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愣神。
而感觉到她情绪的稍稍平复,男人心头的巨石却并未减轻分毫。他小心翼翼地扶住她,让她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。
这几日,她几乎是水米未进,让原本就纤细的身形更是消瘦得惊人。巴掌大的脸颊凹陷下去,下巴尖尖的,气色极差,让雷耀扬痛得揪心。
两人沉默中,他拿起边几上的电话,拨通后嘱咐几句,不多久,家里的厨师亲自端着一个托盘进入书房。
银制托盘上面,是几样精心烹制的、清淡又营养的粥品和小菜,都是极易入口、温养脾胃的。但那股诱人的食物香气,在这弥漫着悲伤的书房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雷耀扬挥退了旁人,自己在齐诗允身边坐下。
他先看了一眼自己那双被厚重纱布包裹、动作极其不便的手,但没有丝毫犹豫地进行下一步。
男人用尚且能动的指节,笨拙却又异常坚定地拿起白玉匙羹,舀起一小口温热的瑶柱鸡丝粥,仔细地吹了又吹,递到齐诗允没什么血色的唇边:
“吃点东西,好不好?”
他的声音低沉而温柔,带着近乎哀求的意味:“就吃一口……”
齐诗允目光涣散没有重点,亦对眼前的食物毫无反应。但雷耀扬极富耐心地举着勺子,坚持着,把声音放得更亲和:
“你不吃东西,身子撑不住…如果阿妈看到,她一定会好心痛……”
听到“阿妈”两个字,女人的睫毛霎时抖了一下,双眼似乎有了一丝焦距。她不禁想起方佩兰过世当时在梦中那些温柔的叮咛,胸腔里濒死的那颗心脏,仿佛有了复苏的迹象。
女人的目光缓缓垂下,落在了那只递到唇边的勺子上,然后,顺着那指尖,看到了那层层包裹的白色纱布。
厚厚的纱布边缘,还能隐约看到渗出的淡黄色药渍和少许干涸的血迹,可以想象,其下的伤口是何等狰狞和疼痛。
可这几日,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巨大悲伤和崩溃中,竟然完全忽略了他也受了伤,忽略了他这双翻云覆雨的手,是为了从废墟中救出她们母女才变成这样———
一股强烈的歉疚擂向齐诗允恍惚的意志,又重重撞击在她心上。
少顷,她缓缓张开有些干裂的唇,接受了那一勺粥。
温热鲜甜的粥滑入喉咙,带来一股久违的暖意。
雷耀扬见她肯吃东西,紧绷的神情稍稍放松,立刻又舀起一勺,仔细吹凉,再次喂给她。
他就这样,用那双极其不便、甚至可能还在作痛的手,一口一口坚持着,极其耐心地喂她。动作已然失了往日的灵活,笨拙中却满载了不容置疑的珍视与呵护。
齐诗允默默吃着,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过他受伤的手。
泪花噙在干涩泛红的眼眶里打转,但这一次,不再是对绝望的宣泄,其中混杂了太多复杂的情感:有对他的心疼、对自己的自责、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楚。
她忽然意识到,沉浸在悲伤中自我折磨,并不能让阿妈回来,反而会让活着的人,让这个同样承受巨痛却还在强撑照顾自己的男人,更加艰难。
阿妈用命护下了她,叮嘱要她好好活下去…绝不是为了看她这样低落消沉。
真凶还逍遥法外,甚至可能正在暗处窥伺,准备下一次的袭击。
除了这个必报的杀母之仇,一个模糊却坚定的念头,在一片悲凉的废墟中悄然萌生。
她需要快速振作起来。
至少,要先活下去。
为了阿妈,也为了…同样伤痕累累的雷耀扬。
现在,自己必须要从这失去至亲的苦海中挣脱出来,哪怕…只是先挣脱出一口气。
揪出真凶,才是对阿妈最好的告慰,也是自己身为人女必须去做的事情。
想到这里,她咽下一口粥,抬起殷红的泪眼看向雷耀扬,声音虽然依旧微弱,却带着暌违的温柔:
“……手,还痛不痛?”
闻言,男人喂食的动作一顿,对上她的目光,愣了一下,随即缓缓摇头:
“不痛。”
他不想让她再担心,她便没有再追问。她只是伸出手,指尖极其轻微地、小心翼翼地触碰了一下纱布的边缘。而这个细微的动作,却让雷耀扬心中猛地一颤,仿佛看到了冰封之下的一丝裂痕。
“…给我吧。”
“我自己可以。”
她轻声说着,顺势接过了他手中的碗和匙羹。
虽然动作缓慢无力,但她开始自己吃东西了。
雷耀扬看着她,心中百感交集,既觉心疼,又有一丝微弱希望悄然升起的感觉。
他知道,这个伤口太深,几乎致命,离真正愈合还很远很远。但至少,她愿意尝试着,从那片绝望的深海里,向外探出一只手。
窗外的暮色渐渐降临,书房里没有开灯,昏暗的光线中,两个人沉默地坐在一起,一个慢慢地吃着东西,一个静静地守护着。
悲伤乌云盘踞,但在那冗沉的绝望之下,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。
那是一种基于共同伤痛和复仇目标的、更加复杂而坚韧的联系,正在重新编织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