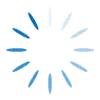怀孕期间,我对他们谎称孩子是高珅的,高珅对此深信不疑,他甚至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给了张瑶满意的彩礼,婚礼就定在月子之后举办。
孩子出生那天,我承受着剧痛,在恐怖的疼痛中笑着将那一坨我认为充满恶臭的肉从体内排出。
我醒过来时,高珅守在床边,领我惊讶的是张瑶居然也在,她微笑着说:“很漂亮,是个女孩。”
高珅告诉我,我生完孩子突然大出血,张瑶不放心所以连夜守在旁边。我说:“是吗。”就没在说话。
我是在家中休养,那是一幢很大的别墅,有喷泉和泳池,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突然给我这么好的待遇。
一周后,我下地了,我抱起孩子,站在窗边,手上拿着刀柄,那是平常削水果用的小刀,只是用来杀一个小孩子的话应该十分利落。
张瑶走进来时,还没有发觉异常,说着婚礼场所已经办妥了,作为新娘的我只需要穿着婚纱接受大家艳羡的目光就行,我对她无话可说。
我在她安静下来时,告诉她这孩子是张序引的,她那张妆容精致的脸顿时僵住。
我平静的脸上默默流泪,问她:“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?”
“为什么要给我这种人生?”
“为什么不让我在出生的那一刻去死?”
我生下孩子那一刻就想掐死她,只是我没有力气了,我全部的力气都用来生产她,接下里的几天我发呆出神,等着力气恢复,我该死的竟然变得心软,我不能心软,这孩子活下来才是害她,在她还没有拥有自己的意识之前,作为我的报复工具死去,是她最好的归处。
“把他们都叫来,把所有人都叫来!”我朝着她凶恶地大吼,手举着带着直指孩子的面庞,仿佛她再不有所行动,孩子就要血溅当场。
张瑶首先给张云卿打了电话,让他通知其他人来医院,她试图问我要哪些人来,我怒吼道:“所有人!所有知道我是什么东西的人!”
聚齐所有人不过只需要半个小时,比我想象中还多,我近乎崩溃了,那些曾给我好脸色当做什么都不知道的亲戚们都聚拢着一块儿。我当着他们的面大声说了怀中孩子的身世,我看着张云卿和那个女人韩叙目眦俱裂的表情,很痛快。韩叙似乎知道张瑶和张云卿之间的旧事,当我把他们之间的丑事暴露出来之后,她并没有跳起来做出要杀人的样子,甚至没有震惊的表情,只是一脸吃了苍蝇般忍气吞声的表情。
我倒吸一口凉气:“你们这群人真恶心,真虚伪。”
我听见不知情的人的唏嘘声,那种另类的打探的眼神落在那叁个还有我的身上,如同麻线圈缠的眼神和人语,就是这种感觉,明明大家都是脏乱差的人,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承受那些视线。
这时,高珅竟然从人群中挤身出来,他似乎在门外听完了我的怒吼,颤着声音问我:“涵意,我们的孩子呢……”
我的心脏在这一刻被紧紧攥着,我还是如实告诉了他:“打掉了。”
“你杀了我的孩子……”他一边说着,一边哭着朝我缓缓走来,我第一次见他哭,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,我无处可退,再往后就是窗户。我眼前起雾,想说别再靠近,但是我的手腕因为情绪不稳在发软,他抬手猛地落下来劈在我的身上,我只感觉脖子传来剧痛,眼前一黑,身子就软了下去。
我再醒过来时,身边没有人,四周的墙面是病态的白,我的四肢被绑住了,我仿佛又回到那个四四方方的昏暗的屋子。那群人将我的手脚捆绑起来,把我的双腿劈开,就让我的生殖器就那么暴露在视线里,供他们依次享用。没有人能帮我,我只能发出呻吟,对他们撒娇,祈求他们能够温柔对待我。
我浑身发抖,仿佛又被抓回了那一片沼泽里,我发出尖叫,像被玻璃刮破的喉咙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。
这时,开锁的声音传来,走进来穿白大褂的男人们,我疯了一样挣扎扭曲身体,恨不得截掉四肢也想逃离这里。
他们没有强奸我,但是他们用电流击打我,我浑身颤抖不止,然后他们给我打针,麻痹我的神经和肉体,我的意识还在,他们给我解绑,抬着我放到另一个地方,把我推进某种机器里,他们每天一天叁顿准时给我用药。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,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,我不敢不听话,我只要挣扎闹腾他们就电击我。就像当初在戒同所,只要我不听话暴露出想要告状或逃跑的意图,他们就会扒光我,强奸我,直到血流不止。
他们正在治疗我。我时常这样半梦半醒被关起来,又头疼脑热的苏醒过来,我感觉我的记忆如同沙漏一般在流失,他们经常测试我一些问题,我一开始准确回答,后来发现我甚至想不起来窗外的飞禽叫什么,不知道睡觉的床叫床,喝的水叫水。但我依旧记得戒同所和我那还没来得及杀死的孩子,仅此而已。
后来我不再回答他们的问题,他们终于带我离开了那间白色的房间,我有了自己的院子,绿色的草地和艳丽的花坛,抬头就能看见湛蓝的天空。
我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回忆那些模糊的东西,我想起来的东西越来越多,但是我表面上还是做出空洞的样子。
天亮天黑,天亮天黑,日复一日,有人来看我了,但是那人从来不走近,远远地看着我。起初我不知道那人是来看我的,后来我发现那人总是隔一段时间就出现在那个位置,我知道,他大概是来看我的,只不过我想不起那张脸是谁,或许他是我记得的名字里的其中一个人。
我像是行尸走肉一样,天天在这一块天地反复走动,我唯一的乐趣就是经文,各种各样的经文,那些人好像致力于洗涤我,他们不给我其他任何打发时间的东西。不给我纸也不给我笔,食物也很清淡。我想了好久,才想到一个可以形容自己的词汇,“出家人”。
这天,突然很吵,我撑起身体专注地听着外面的动静,那扇只有医护人员可以进出的门被从外面猛地撞开了。
那个男人在看见我的那一刻露出激动的笑容,而后双眼通红冲向我,那些人根本拽不住疯狗一样的他,他双手铁钳一样焊在我的肩膀上,要把我的内脏和脑浆都晃出来:“张涵意,你躲在这里!我的孩子呢!你生下来的孩子呢!”
我除了发蒙地睁大眼睛盯着他,给不了任何回应,之后又冲进来一个男人把他打翻在地,两个人就那么扭打了起来,我认出来了后来那个男人,他就是经常站在远处眺望我的男人。
我头很疼,直到房间安静下来,再次被锁上,我才想起来和那张脸对应的两个字——高珅。
经过被突然闯入这件事后,我被带去了另一个地方,用半天的路程。
我在这里还是有自己的院子,我在这里安静地度过一天又一天,我时常忘记自己的名字,在那个人指控我疯狂地问我孩子在哪里时,我想起来,他口中的张涵意好像就是我。对,我叫张涵意。
孩子?他说的是我没来得及杀死那个孩子吗?我很混乱。我不止有一个孩子吗?
我甚至想再见他一面,我这样想着,屋外又传来了喧闹声,我看见了破门进来的他,又是他!不过这次他没来得及靠近我,就被架起胳膊双腿抬了出去。
在那之后我又被转移了地方,这次我看见了她,我看见她的一瞬间就想起来这个人是张瑶,是我的母亲,我看见她心脏就变得很痛苦,像是站在悬崖边上,而张瑶是那个绝对会推我一把的人。我瑟缩着,躲开她的视线,她却朝我走过来,她的目光是冷峻的,没有感情的,仿佛我是一个只会添麻烦让人不得不冷眼相待的人。
她看了我一会儿,没有任何言语,转身要走,我突然伸出手抓住了她,我发誓我没想过要阻拦她离开,是我的胳膊不听使唤,我的嘴自己就张开了,说了大脑想知道的问题:“孩子呢……孩子……”
她甩开了我的手,冷眼看着我,说出来的话却不冰冷:“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活的好好的。”她似乎还想说什么,却严严地闭上了嘴,彻底转身走了。
我闭上眼睛睡了很久,做了很多破碎的梦,我在梦里缝缝补补,睁开眼,我想起了那不堪的过去。我恨自己,为什么一定要想起来才肯罢休。我开始睡不着觉,然后身体支撑不住突然晕倒,我总是睁眼到天亮,连续夜里也不睡,白天双目刺痛也要睁眼空坐着,在突然的时间晕倒过去。
这天,我依旧守着天明,站在院子里,我像只壁虎一样爬上了墙壁,我的手指被磨破,全是烂肉,马上就要翻过去了,马上。我还是被抓了回去。但我翻墙成功了,我摔得呲牙咧嘴,但是外面的工作人员看见我就立刻把我带回房间、锁在房间里。
我被关了一个星期,他们再把我放出院子时,我发现,那面墙高了两倍不止,新的涂漆颜色更深,鲜明的把我困在这一处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他们竟然放我出了院子。我来到一片更加宽敞的平地,这里似乎没有人,有密集松林和石墩,我看见有一条长长的白色椅子,我走过去坐下。
他们就守在不远处,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突然拓宽了我的活动空间,但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偶尔就会有这样的待遇,离开那一片院子,来到这个更广阔的地方,我的心境变得开阔了很多。但是无法遗忘的往事总是像针一样戳刺着我,我无法彻底放松下来,我总是想着离开这里,我还有没有完成的事情。
这天,我看见远处站了两人,我一眼就认出来那个男人是高珅。他身边的人是谁?我从长条椅上站来,朝那边走去,他们似乎发现了我的动向,两个人牵扯着藏身到我看不见的地方。
我隔着遥远的距离,在空气中张了张嘴:“慕……淳……”
我已经好久没说过话了,我感觉有咸涩的东西滑落进嘴里,我咽了下去,是前所未有的苦涩。
我回到院子,啃着手指,像一只迷途的大象,在原地打转,我这样转了好几天,我的所有指甲都被我啃秃了。
墙面上的爬藤已经密密麻麻长满了,我之前时常和那些护理女士玩捉迷藏,我躲在那些藤蔓后面,她们很难找到我,然后我会突然出现在她们身后,吓他们一跳 像个疯子一样倒在地上摇摆四肢。
我看着那些爬藤,快速走过去疯了一样把它们掀开,不管那上面的倒刺扎进我的肉里有多深。
我突然呵呵发笑,我感觉我的机会来了,她一定还会再来的,慕淳。
我去房间找一些还算坚硬的东西,开始对着那一面墙狠凿,我凿那个洞凿了很久很久,我的手破了一次又一次。其实大小早就能容下我的身体,但是我在等着她,我无法安静下来,我天天都去凿一点,洞口越来越大,那样我可以跑得更快。
在我以为她不会再来的时候,我的门外再次传来恐怖的撞击声。我没搭理,我大概知道是谁,所以在他进来后,我抬头望向他,说出了他的名字:“张……序引。”
再后来,她出现在我身边保护我,在我可怜的求助下,通过我挖的洞口带我离开了那幢白色的建筑,我自由了,我马上就要彻底自由了,她要带我去见那我来不及杀死的孩子。
她似乎很防备我,时时刻刻紧盯着我的动向,我知道我一定得做些什么来降低她的警惕。
我是一个渴望见到孩子的母亲,母亲想体面的去见那可怜的一出生就与母亲相隔的孩子。于是,我这样做了,我让她给我打扮,见到孩子后我痛哭流涕,我时刻都想和孩子亲密相处,我把孩子当做我的主心骨,我亲切的给她们作羹汤,我使劲浑身力气让她、让她们接纳我。
在她转身去厨房那一刻,我知道,我的唯一的机会来了。我抓起那孩子就冲出了门,我的心脏就要跳出胸膛,电梯门打开不过一瞬间的时间,我拖着那孩子进去,疯狂按关闭键,逐渐合拢的电梯门终于切断了她惊慌失措的视线。
我捂住孩子的嘴,直到电梯停下来,我拽着那孩子到了天台的边缘,风不是很大,但是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吹胀气的气球,随时都要飘起来,那是即将摆脱一切的轻松,我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,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。
我本来想直接就这样跳下去算了,但是我还想再和她说两句话。
她果然没有爱过我。她追上来,可始终紧盯着我身边的孩子,她的回答没有一个字让我满意的,让这种时候还在期待她的我变得十分可笑,我一直这样,像个小丑一样跳来跳去,到死都是。
当她那么自然的躲进那个男人怀里,我恶心到反胃,我多后悔没有直接跳下去,居然让我见到这种万恶不赦的画面。我痛恨她,她怎么可以走上那条路,她看不见我有多痛苦吗?
那一刻,我切实感觉我身边至始至终没有一个人,所有人都在背叛我。他们做的事,仿佛都只是在对着我呐喊,去死,快去死吧。
我辱骂她,希望她可以醒悟过来,我死去,然后让她醒悟过来吧,像做梦那样,只是一场梦而已,不要有负担。
“你不得好死!”我刚说完这句话,那孩子就把我推下楼了。
太可笑了,但我来不及嘲笑自己。
那一瞬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感受,但是我闭上了眼睛,那一刻我在落下,又仿佛是在被世界举起。我的感受是,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前所未有的轻松。
最终我落下了,我感觉我是翩翩坠落的,像落叶、羽毛或者蝴蝶的翅膀?
我感觉我在微笑,落在地上的破碎的我是在微笑吗?
我轻如鸿毛,活着的时候是这样,死去的时候也是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